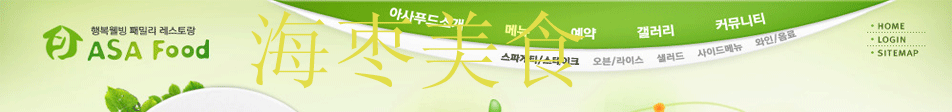|
故乡的记忆 焦文琦 年轻的时候,多憧憬未来。到老之时,却多于怀旧。回忆往事,几乎占据着整个心田,而扑朔迷离的往事之中,那儿时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石房土院,人情事故,数得上最清晰的记忆。 我的家乡,是一个六七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坐落在冀西太行山间、滹沱河南岸的小山沟里。山上沟里多花岗岩、片麻岩,呈整体状,固若盘石,叫盘石沟。 盘石沟南北走向,分东西两沟,沟深十余公里,左转右拐,足够九曲十八弯,分布着东西南北四个盘石,我的村子东盘石就在五曲九弯上。村南的山峦像一只昂头展翅的凤凰,村北的山脉似一条起起伏伏的长龙。一条淙淙的小溪自东向西穿村而过。村中的独孔小石桥连接着两片平、瓦混杂的房舍,真可谓“小桥流水人家”,凤翔龙伏风脉! 已有四百年历史的小村,因为地处山沟小处,没生长出富门大户。村中一无祠堂,二无家谱。传承文化的唯一方式也教奇特:热天,乡亲们端着蓝边海碗,凑在小街的树荫下,一边吃饭,一边谈天道地;冬天晚上挤到羊圈里,一边用烟袋锅吧嗒吧嗒抽着旱烟,一边说古论今。一辈又一辈传下来,便知道了小村的来历:明朝末年,李、韩、焦三姓从周围三五十里的村子相继搬迁而至。一辈又一辈的能如数家珍般地讲出韩家长、李家短的历史掌故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上天的恩赐,大自然的造化。大麦、玉米、稻谷、杂粮,一年两季,样样皆有曰大枣、柿子、核桃、花椒、桃、梨、杏五果十全。牛、羊、驴、骡、鸡、鸭、猪、兔,畜禽满圈,山上狼虫虎豹经常出没,沟里野兔、野猪、獾到处乱蹿,家畜家禽时有被伤害的威胁。养只猎狗,紧栏闭圈,即能得到防范。因此,人兽共存,相处自然。 守着山沟,傍着小溪,祖祖辈辈,一把镢头,一张铁锨,一担摘筐,一条扁担,大山里走,坡坡上爬,饿了摘把酸枣,渴了掬一捧泉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觉得,比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还美十分。 春天,小溪还未解冻,那溪边的柳芽却已黄绒绒的。父亲腰里掖把镰刀,三攀两攀登上树杈,砍下一些枝条,我便把那嫩芽捋进筐儿里,挎回家去,母亲放进锅里添上水,烧火一榨,再滚些小米汤,作浆水一糟,三五天便能调着吃,调时放些椒籽油,又麻又酸,那可口,那美味,至今想起来,还直流口水。 暑伏时节,掀开瓮盖,挖一碗黑枣面,用刚打来的冰凉井泉水,盛满一盔,将枣面放进一搅,舀上一碗,一饮而下,那清爽,那甘甜,顿时让你祛热落汗。 冬天活儿闲,只吃两顿饭,割一担山柴回来,爬上屋顶,扒开玉米秸围盖着的红红的软柿,稀溜溜的,一连吸上几个,真是个透心凉啊! 还有那块状的枣瓣面,结着一层厚厚白霜的柿饼、柿桃,都是我上学的主要干粮。在我的心目中,如今五星级饭店的美味佳肴,永远也无法代替儿时家乡的粗茶淡饭,以及柿干、枣面烙在我生命中的记忆。 盘石沟,以她独特的地理风情,造就了山里人坚若磐石,淳朴善良,虚怀若谷的秉性。生活中免不了遇到沟沟坎坎,天灾人祸,再苦再难腰不垮。说话直来直去,待人热情厚道。邻里街坊,和睦相处。偶尔也有磕磕碰碰,争争吵吵,争吵过后,烟消云散,从不小肚鸡肠。一家有难,大家帮,一家好吃,大家尝。 谁家择了良辰吉日,为儿子娶媳妇,这可是全村最喜庆的日子。不出五辈的同族人都来当值客。提前三天就忙活,劈柴、担水、蒸馍馍,碾米、推磨、做豆腐,摆荤席的还杀口大肥猪。 过事那天,新娘进村三声炮,迎亲的大喇叭嘀嘀嗒嗒吹起来。本来就不宽敞的小石街挤得水泄不通,还有的站在碾盘上、房顶上,争着一边观赏新娘的芳容,一边咬耳嚼舌地评论。 这时,一年轻嫂子端来一筐粘糕,人们就一轰而抢,粘糕掉在地上,抓起来就吃,哪管它有沙有土。据说,抢粘糕的场面越热闹,这家的媳妇粘得越牢,小两口的小日子会像芝麻开花越开越高;吃着糕的人,也会喜事不断。 中午开席,喝酒菜六个、八个不等。一色的自制红烧枣酒,主食有大米、馍馍,主菜是红烧肉、炸豆腐、炖粉条、熬萝卜块一共八大碗。吆五喝六地划拳,香香甜甜地海吃,从中午一直到红日偏西,接着晚上闹新房。 新媳妇三天没大小,但新房闹得也不俗。小小的新房屋,烫烫的土坯炕,炕上地下都是人,好耍的人端着小油灯,照着新娘的脸蛋,让大伙儿看眉、看眼、看嘴唇,逗她说话、唱曲儿、扭屁股。若不是嫂子辈的来撵,一定会闹到大天亮。 年长一点的走了,与新郎年龄差不多的留下来听房。特别是没结婚的和结不了婚的光棍儿,耳朵紧贴着窗棂纸,屏住呼吸,仔细听着屋里那一丝一毫的细微动静。 谁家老人过世了,这又是全村最悲壮最尊严的日子。这一天能把平时的恩恩怨怨一下子化为乌有,全村老少都前来吊孝,家家户户都尽力帮忙。我大伯阔别故乡几十年,虽然当了官,却没给村里办丁点儿事。他去世后,我护送灵柩回故乡,乡亲们迎出去好几里。 到家里,灵堂早已安置好,院里几口大锅里冒着热腾腾的香气,请客的一切准备都停停当当,就连迎魂幡、孝子棒都糊好了。发丧时,乡亲们争着抬棺柩,把鞋子踩得满街都是。 事办完之后,我跪在老少爷们面前,替走了的大伯道谢。话没出口,就被二大伯吆喝起来:“什么也别说,你大伯生是咱村的人,死是咱村的鬼,落叶归根,入土为安,大家帮忙,这是老规矩!” 逢年过节,农历三月二十的庙会,更使我难于忘怀,记忆犹新。孩童时,最盼着过年。一过腊月二十六,满街筒的孩子们,都在可着嗓子喊:“今儿七,明儿八,外外后儿,大年下。大年下,烧香磕头,放炮仗;羊肉饺子,花衣裳!” 大年初一,全村人争着第一个到村西青砖灰瓦红柱子的山神庙里烧香。据老人们说,谁家抢了第一,谁家就有一年顺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口安康。 据说,老辈子那会儿,有一个叫焦建功的,有一年他是最后一个进庙烧香的,结果没出正月,狼就把他家小猪仔叼走了。于是,他赶紧到庙里赔礼道歉,重拜神灵,许下三月二十庙会上,供奉全猪一口。 庙会正日,焦氏牵着他家的老母猪来到山神跟前,跪在地上,口中念念有词:“山神爷爷,俺焦某说一不二,今把活猪牵来,请你领受。”说完,还把带来的半瓶子枣酒,灌进猪耳朵,要等猪摇头摆耳,才算山神爷领受牺牲。 谁知老母猪一动不动,焦氏感到惊奇,但方寸不乱,开口又道:“你是庙里山神公,我是盘石焦建功,只是许你猪一口,当时没说母和公。”说来奇怪,话音刚落,那母猪把头扑楞楞地摇摆三次。看来神灵也认理。那一年,焦氏一家除了狼叼猪娃,一年运气颇佳。 后来,庙已成废墟。废墟上垒几块砖,搭一张石棉瓦,让山神将就住居。不过,三月二十的庙会年年唱戏。唱戏时把山神用黄纸写个牌位,请到村里,面对戏楼围个席棚,点上蜡烛,烧上柏香,一边让山神看戏,一边接受村民许诺。 盘石沟,平山淳朴民风的浓缩和象征。盘石沟,我永远的家,永远的爱! 作者系平山县文化局原副局长、《百合花》主编,多篇文艺作品在国家和省市获奖。 主管:平山县文学艺术联合会 主办:平山县文艺评论家协会 总编:付金龙 本期编辑:关新 邮箱:psxwyp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