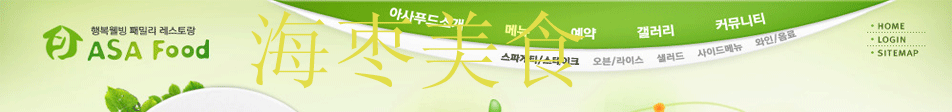|
对两次世界大战间法国军事战略的影响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要塞与筑垒地域的完备程度饱受诟病,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国(也可以说是比利时)在边境线上修筑的一系列要塞与筑垒地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看似老旧的防御体系甚至可以说拯救了法国。这种相对成功的战争经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一战后法国的军事战略走向,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在一战结束和凡尔赛体系建立之后,欧洲大陆自普法战争后形成的德、法、俄、奥四强鼎立的原有政治格局被打破,德国战败投降,奥匈帝国分崩离析,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处于同国内外反动势力殊死搏斗的危急状态当中。唯独法国成为了主要的战胜国,因其对手的削弱和瓦解而显得突出起来。但是,战胜的法国掩饰不了战后的虚弱。一战四年战火,法国军队阵亡多达.7万人,有多达万人伤残。在战争中,法国有十个省份被德军占据,德军劫掠了那里大批的工业设备和工业产品,再加上战火的毁坏,法国遍地战争疮痍。法国近2万家工厂、公里铁路和5.3万公里公路遭到破坏,煤产量从战前的每年万吨下降到战后初期的万吨,内外债务多达亿金法郎。 战后初期担任法国外交部部长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Briand)形容他的国家面临“荒废破产”的境地,而此时国际上法国的外交地位也并不稳固。年之前,法国依赖其雄厚的实力可以和欧陆上任一强国单独抗衡。但是自普法战争之后,法国经济发展缓慢,人口数量停滞不前,在列强工业化以及相应的军事力量的竞赛中,法国滞后了。欧洲中部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崛起,法国感到自身的国家安全无力独力保障。于是乎,法国的防务政策逐渐从独立走向依赖,将建立联盟看做国家战略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事实上,直到19世纪90年代与俄国结盟、摆脱了20年的外交孤立之后,法国在国际舞台上说话的声音才得以增强。 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Briand) 此人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界的常青树,曾经11次出任总理,以对德和解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非战公约和倡议建立欧洲合众国而闻名于世,年其出任外交部部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在得到英国、俄国、意大利以及后来美国的援助之下才勉强战胜了寡援少助的老宿敌德国。而在战争结束之后,法德两国战争潜力的天平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德国仍然体现出远比法国更强的战争潜力。因此,寻求盟友仍然是法国坚定的信念。 然而,由于俄国在一战中爆发了革命,退出战争,法国由此丧失了其在欧陆上的主要盟国。一战后初期,法国又领衔对苏俄进行了军事干涉,加之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反感和厌恶以及苏联自身的国内问题,同苏联重新结盟的前景黯淡。因此,法国从传统的欧陆同盟转向大西洋同盟,求助于海洋那一头的英美两国。巴黎和会上,法国忍痛以莱茵兰问题的妥协为代价换取英美对法国国家安全的保证,孰料节外生枝,后又未果。在欧陆同盟和大西洋同盟均未能实现的困境中,法国退而求其次,转而同中东欧国家结盟,构筑所谓的反德包围圈——小协约国。理论上,法国的这些中东欧盟国实力并不差,实力总和强大,但是这样简单的累计并不能反映问题的实质。这些国家,一则多是农业国,经济力量脆弱;二则彼此之间纠纷重重,积怨甚深。因此,这样的同盟极为脆弱,它难以弥补一战之前与俄国的同盟关系。因此,法国一面保持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一面又时常把注意力转向实力更为雄厚的英美,尤其是把近邻的英国视为潜在的同盟者。 二战前夕波兰装甲兵的7TP轻型坦克 二战的开局证明,法国在一战后着力结交的中东欧国家实力上弱小,往往沦为强国的抹脚布。 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及30年代初,英国对于欧陆重新执行19世纪的均势政策,“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几乎在所有问题上与法国发生矛盾与冲突,使得法国在政治和外交上屡屡失利,求助于英国的愿望非但没有达成的同时反而削弱了自身的地位。 与此同时,由于地理上的因素致使法国的这种困境进一步加剧。法国的重工业和重要的矿产资源多分布于东北和北部。在敦刻尔克、斯特拉斯堡和巴黎的三角地带,这里出产法国75%的煤、95%的铁矿石,法国大部分的重工业也集中在这里;在巴黎、鲁尔和里昂的三角地带,这里生产法国90%的布匹和80%的毛制品以及大部分化工产品,所有的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也集中于此地,而这些工业中心周围居住着相当多数量的人口。然而,紧邻其旁的德国对于这一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地区构成了最严重最直接的威胁。年普鲁士对拿破仑的战争以及年的普法战争,来自于中欧的入侵者都是经由洛林进入法国的。因此,守住此地,即意味着阻挡了德国的直接入侵,不仅保障了法国的战争能力,很大程度上也就保卫了法国国家的安全。更何况,保护法国东北和北部地区,实际上超出了一般守卫边疆本身的意义,成为影响法国全局的重大事情。对此,20世纪30年代早期担任法国陆军总监马克西姆·魏刚(MaximeWeygand)上将说:“任何欧洲冲突的关键都在我国东北方的国境线上,所以问题就在于坚守这一线。” 马克西姆·魏刚(MaximeWeygand) 如何保卫法国的东北边境进而维护这个国家的安全呢?这事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整个防务政策的措置。一战爆发之前,法国在对德战略上采取纯粹的攻势姿态,其在战前制订的十七号计划更是将攻势思想发展到了顶峰。遵循这一计划,法国在战争爆发之初醉心于强攻猛打的战法,结果损失惨重。由此,十七号计划不得不废弃,法军只好转入绵延数百公里的堑壕同敌人展开更为惨烈的阵地战,战前所估计的速决战被长久的消耗战所取代。事实证明,一战前的法国战略思想并不符合战争发展的实际。 一战结束后不久,由亨利·菲利浦·贝当(HenriPhilippePétain)元帅和玛丽·尤金·德伯尼(MarieEugèneDebeney)将军等13人组成的法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在总结一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拟定的法国军队的“圣经”——《使用大兵团作战暂行条令()》。该条令对未来战争做出了预测:第一,未来法德战争将是长期的总体的较量,“兵员和武器的巨大发展造成的花费和复杂性进一步加剧,使得战争真正总体化”;第二,进攻只能在实力占据压倒性优势时才能实施,攻势一方要具备“三倍的步兵、六倍的火炮、十五倍的弹药”;第三,第一次马恩河会战前的诸要塞滞阻战、第一次马恩河会战本身以及凡尔登要塞防御作战但是成功的防御样式。这意味着对战前军事学说的反思与对一战经验教训的吸取成为法国一战后战略决策的重要思想源泉。 玛丽·尤金·德伯尼(MarieEugèneDebeney) 除此之外应该看到的是,在一战中大批青壮年的死伤对于战后的法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压力,源自堑壕的和平主义思潮和运动由此也拥有了广大的市场,迅速地在全国流行起来,并且经常反映到相应的政治和军事决策之上。法国社会反对战争、要求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浩劫的巨大力量连同军方的上述总结,法国军政高层很自然地得出处于相对劣势的法国同德国的未来战争应该采取防御战略的结论。而又由于凡尔登战役的巨大影响以及这一战役的指挥者贝当元帅的显赫地位,这种战略思想变得牢不可破了。 那么究竟要如何打一场防御战争?一战中,一连串成功或是接近其成本的要塞防御的经验使得法国修筑永久性国境要塞的传统获得了新的活力。于是乎,法国沿德、法、比边境一线修建一条现代化永固筑垒地域工事的计划也就顺其自然地产生了。 马奇诺防线分布图 红色实线为已经修建完毕的防线,红色虚线则为靠近比利时未完成部分。 事实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刚刚熄灭的时候,法国军方就忙于筹划下一次战争的对应措施,其焦点便集中在边境防御问题。围绕着防御工事的目的、类型和地点选择等诸多问题,法国军方在20年代20世纪初即展开了热烈持久的大讨论。整个讨论过程因鲁尔事件而被分为两个阶段。年5月,法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在成立之后第一次聚会以研究国土防御问题。与会者各抒己见,众说纷纭,而讨论的唯一结论是各位委员继续研究国土防御问题。会后,法国陆军部组成了以约瑟夫·雅克·塞泽尔·霞飞(JosephJacquesCésaireJoffre)元帅为主席的“设防地区研究委员会”,研讨边境防御的措施。该委员会在进行了实地考察之后,提交了《关于国土总的防御编成的报告》,认为法国建立的边境防御体系应该在北海到阿尔卑斯山之间修建一些强大的间隔的筑垒地域,在它们的掩护下,野战集团军实施机动,等待有利时机展开反攻。 对此报告,身为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贝当元帅提出异议。年,贝当在提交的《关于国家防御编成的报告》中认为,法国防御的答案在于确立现代防御体系,这一体系是在和平时期沿整个东北边境建立的“预设战场”,形成“绵亘的战线”形式,法军坚守在阵地中,准备迎击敌军。同时,防御体系的目的是用来保护国土的不可侵犯。而斐迪南·琼·玛丽·福煦(FerdinandJeanMarieFoch)元帅则反对这一观点,他在年5月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强调,法国的领土过去是由机动的陆军守卫的。霞飞和福煦的意见一致。 斐迪南·琼·玛丽·福煦(FerdinandJeanMarieFoch) 该照片为其年担任第35炮兵团团中时所拍摄,其所在的福煦家族是拿破仑家族的旁系。 到年中,边境防御的两种主要观点进一步明确化、系统化。第一种意见,以贝当元帅和总参谋长埃德蒙德·里昂·比亚(EdmondLéonBuat)为首主张沿边境建立一条连绵不断的防御工事,这种工事由堑壕、铁丝网、机枪阵地构成的预设战场,把绵亘的防线与静止的防御结合在一起;持另一种观点的则是福煦、霞飞和玛丽·路易斯·阿道夫·吉约马(MarieLouisAdolpheGuillaumat)等人,他们建议采用间断的筑垒地域作为抵抗中心以便陆军反攻,围绕这个抵抗中心的陆军实施机动,寻找合适的时机和最有利的条件发起反攻。两种意见之争直接反映了一战后法国军方两种学派的冲突。一派是以贝当为首的以凡尔登战役经验为依据的防御论者,认为依托工事防御是战争胜利的关键;另一派则是以福煦和霞飞为代表、主张机动进攻,其思想源泉是对战前军事思想的继承和战争最后阶段攻势取胜的经验总结。 埃德蒙德·里昂·比亚(EdmondLéonBuat) 年秋,两种观点的阵营进一步分明。最高军事委员会内部较多人倾向于既能攻又能守的防御体系,而对于预设战场的思想表示怀疑。然而,双方仍然互不相让,各执一端。于是乎,法国陆军组织了一个“国土防御特别委员会”继续研究。该委员会先由霞飞担任主席,而后则被吉约马取代。在一段时间里,这个委员会成为了双方争执的中心场合。年末和年初,该委员会在讨论保卫边境的种种方案时,形成了以吉约马和比亚相对立的两派,仍然围绕上述争端争执不休。年1月,鲁尔事件爆发,委员会工作暂停,直到年春才重新着手进行。第一阶段的正式讨论无果而终。在鲁尔事件之后,双方争论进入了新的阶段。由于年秋比亚将军去世,委员会中失去了最主要的“抵抗中心”说的反对者,兼之新任陆军总参谋长德伯尼将军支持吉约马的观点(不过德伯尼更赞成筑垒地域的抵抗中心是防御的而非进攻的),形势明显朝着有利于筑垒地域的“抵抗中心”说发展。 玛丽·路易斯·阿道夫·吉约马(MarieLouisAdolpheGuillaumat) 年12月,吉约马将结论报告呈交最高军事委员会。该报告中论证了“预设战场”的弊端,否定了贝当关于“预设战场”的设想,肯定了筑垒地域作为抵抗中心的重要意义。最高军事委员会对该报告进行了审定,终于同意防御体系建筑的形式应是非连续的筑垒地域,但是并没有像吉约马所说作机动进攻之用。于是乎,双方在防御体系的总体目的上继续存在分歧,贝当坚持他的观点,防御工事将保护领土“不受侵犯”,福煦则针锋相对地强调:“工事不应该具有保护国土不受侵犯的安全目的,而是面对敌人进攻时保护部分的集结。”前者把国家的安全寄托于防线之上,绝大部分兵力在防线后分兵扼守,防线便是决定性战场。后者则是以防线作为前进基地或出发地域,打一场机动的防御战。双方争执不下,悬而未决。 马奇诺防线各堡垒要塞分布图 20世纪20年代后期,形势逐渐发生了有利于贝当一方的变化。在年底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上,贝当对于边境防御委员会提出的要塞使得进攻行动更为便利或者成为向法国心脏进攻力量的聚集地的意见进行批评。贝当宣称,法国当然希望使用进攻手段把战争引向莱茵兰,但是当被迫从德国的土地上最终退回来时,形势将更为不利。因此,筑垒要塞在条件允许进攻之前,至高无上的是防御。而吉约马则激动地表示:“要塞不应阻止进攻。”双方未能达成一致。但是会议的进程表明,赞成要塞作为进攻基地或是出发地域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 马奇诺防线内部构造图 自此以后,防御工事作为进攻手段的呼声越来越小。其原因除了福煦和霞飞因为年老体衰而退出决策使得进攻派力量大为削弱外,还有两个客观原因。一是《洛迪诺公约》规定协约国军队提前从莱茵兰地区撤军,法国丧失了进入德国的桥头堡,因而用进攻手段把战争引向德国土地上进行的难度增加;二是年法国新征兵法案的效应开始显露出来。由于即将实施一年兵役制,基干部队人数锐减,法军在战争开始阶段将无力发动进攻行动。因此,法国军事当局得出结论,任何对德战争必须包括两个阶段。第一,掩护部队作战阶段,此时只能保护边境并进行国家动员;第二,民族斗争阶段,倾整个国家的资源、人力抗击敌军。因为法军主要力量为预备役军人,他们的训练时间短,水平低,难以达到进攻所需要的技术素质,进入工事打防御战则更适应其特点。因此,贝当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防御工事也就被军方视为纯粹的防御手段,并且被当权的贝当等防御派逐渐上升到“保护国家不受侵犯”的安全目的高度,即把国家安全的赌注全部押在了防御工事之上。 马奇诺防线地下工事内装备的81mm迫击炮 值得注意的是,当不发射或是装弹时,射击孔可以关闭,用以提高隐蔽性与防御性。 年10月12日,最高军事委员会正式采纳了贝当所拟制的设防方案。边境防御方案通过以后,年2月,法国军方在三个试验地段动工,并且对于试验结果颇为满意。年11月,法国军方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促使国会在年初通过了防御工程的预算拨款,于是防线全面动工。年底,绵延数百公里的地下钢铁长城基本竣工——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马奇诺防线。 结语 军事艺术固然是一部发展的历史,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是大势所趋——从技术到战术、战略莫不如此。然而同时也应当看到,新事物取代旧事物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种转变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也正因为如此,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机械化战争已经开始崭露头角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自中世纪便富有筑堡传统的法国、比利时等西欧国家仍然利用或完备或有欠完备的要塞、筑垒地域,进行了一系列相对成功的军事作战。这些作战的结果,不但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产生了关键性影响,也影响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的军事战略走向。 本系列往期回顾: 炮口下的磐石——从中世纪的筑堡艺术到一战中的要塞、筑垒地域(卷首语) 炮口下的磐石——从中世纪的筑堡艺术到一战中的要塞、筑垒地域(1) 炮口下的磐石——从中世纪的筑堡艺术到一战中的要塞、筑垒地域(2) 炮口下的磐石——从中世纪的筑堡艺术到一战中的要塞、筑垒地域(3) 宋华阳赞赏 |